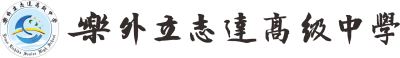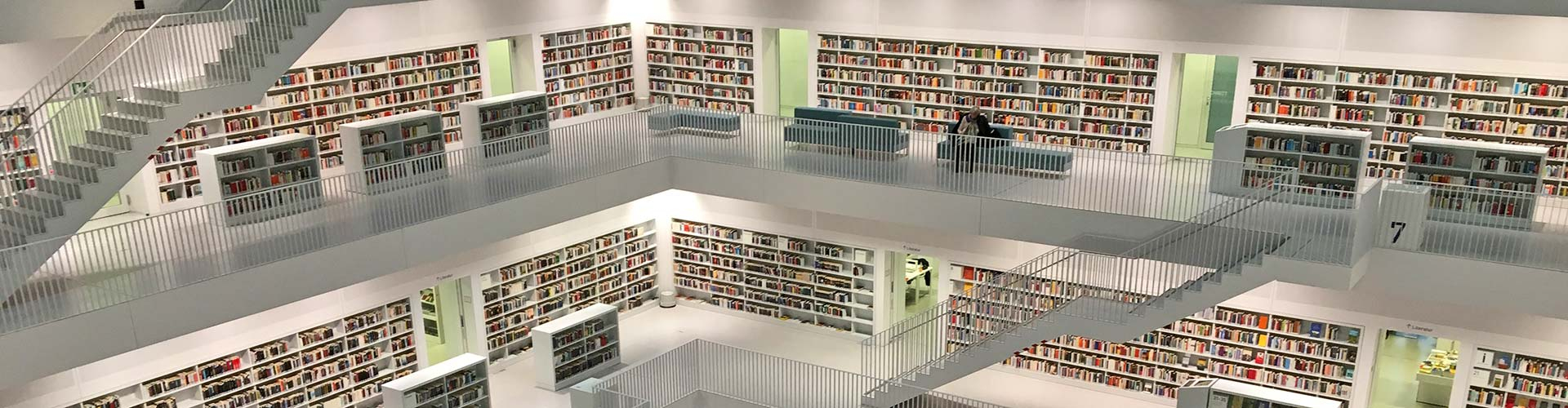笔者在解读和讲解《归去来兮辞》时,总绕不开陶渊明的在文中的行踪一问。我们能从文中诗句中寻到一些明显信号。“舟遥遥以轻飏” “问征夫以前路”诗人在归途之中,到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诗人欣喜望见家门,一路奔跑归家。“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走进庭院,“携幼入室”进入居室,到“园日涉以成趣”从居室中走到庭院。归家途中——望见家门——进入居室——走进庭院的行踪清晰。下个段落 “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到郊野游玩赏万物,行踪也有迹可循。但“抚孤松而盘桓”一句,作者是在庭院内还是已经走出庭院,走到了郊外了呢?“抚孤松而盘桓”一句处于二段末尾,连接第三段,在全文结构上起到桥梁与过渡作用,弄清楚此句的游踪,对诗人全文的游踪有着重要意义。对此,笔者做出诗人在庭院中和诗人走出庭院两种假设,以探究诗人全文游踪。
一、 诗人在庭院中,抚孤松而盘桓
(一)遐观之“景”抚孤松而盘桓
诗人在庭院中时,并非自己抚孤松而盘桓,而是“景”,即太阳。王启钢(2010)中认为“抚孤松而盘桓”一句的主语应当是 “景翳翳以将入”的主语“景”,即太阳。此处的‘抚’当是一种拟人用法,以描摹夕阳流连的情态。王启钢从诗人写诗背景以及上下文情感的衔接两个方面证实“这样写多了陶渊明对大自然的一种最真切的理解和全身心投入自然的向往,少了一些愁绪。” 由此,“云无心以出岫”四句皆是诗人在庭院中昂首远观之景。
(二)遐观“景”,诗人于庭院中手抚孤松盘桓
文章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两句中,“松菊”并非无心栽种,作为庭院的色彩点缀其中,还是诗人精神品格的外化表现,诗人借此表白自己的心愿。沈纳新(2020)谈到,陶渊明的庭院内遍植“松菊”,“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畏严寒是松的坚韧品格,在庭院中种松树,自然寄予了主人对于坚强、坚韧、不屈人格的追求。那么,“抚孤松而盘桓”的“松”与上文“松菊犹存”中的“松”便是同一“松”,诗人两次将“松”置于笔端,种松树、抚孤松,是为了强调自己傲岸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刚正品格。
同时,“抚孤松而盘桓”还承接上文诗人在庭院中的活动。人教版语文必修5《教师教学用书》中的解读是“作者将笔锋从写居室转到了写庭园,甚至到高处、远处等目光所及之处,精心选取了‘园日涉’等几个画面,表现出隐逸生活的无尽乐趣及作者的孤傲坚贞之气”。[3]《古文鉴赏词典》[4]中吴战垒也认为第二段由居室到庭园,作者写出了怡颜悦性的情事和令人流连忘返的景色。暗示自己的精神品质,承接上文的活动并抒写多个悠闲画面,这样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的行踪仍在庭院之内。
二、 诗人走出庭院,抚孤松而盘桓
人教版必修5《归去来兮辞》中将“流憩”一词译为“流,周游。憩,休息。”“策……憩”的释义为“拄着拐杖出去,到处走走,随时随地休息”,必修5《教师教学用书》中译为“拄着手杖走走停停,到处游息,不时眺望远景”。《国语词典》中将“流憩”一词解释为“到处游玩或稍作休息”。“周游”“到处游息”“到处游玩”都指明诗人的活动范围较大。
那么,诗人到底在哪里“流憩”呢?“审……安”一句中诗人以无法安放双膝的夸张手法极言居室狭小,接着写到“园……趣”,从居室走到庭院,甚至每日涉园成了一种乐趣。那么,庭院是否与居室规模相反,能满足诗人的“流憩”呢?陶渊明从走出家园开始,一直厌恶官场,心向田园,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十一月辞去彭泽令,正式开启他的隐居生活。后(408)年因家中失火,宅院尽毁,被迫迁居。这三年间,陶渊明以《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记录自己的躬耕生活。他在诗歌中这样记录自己的房屋:“方宅……,……,……,……前” 。王九卿(2014)认为“方”应根据吴铜运主编的《高中文言文译注及赏析》中的解释,为“四周、周围”之意,将“方……亩”释为“住宅周围有地十多亩” [8]是一种合理的注译。住宅周围即为庭院,堂前桃李罗列,后檐榆柳荫庇。“采……下”、“青松在东园”“东园之树”、“松……存”,东边有东园,园中有松菊。这十余亩方宅都掩映在一扇“荆扉”之中。充盈的院中景象,似乎能满足诗人“流憩”的目的,窥见诗人涉园的乐趣。
若是在园中“游憩”,又何需“策扶老”呢?东晋义熙元年(405),陶渊明(约365-427)约40岁,正值壮年,在庭院中近距离地游赏还需拄着拐杖吗?“不病不老,拄着拐杖出门或下地,却又想要表达旷达飘逸,这就矛盾。”邓福喜(2019)为陶渊明的“扶老”重新下了定义:“扶老”不应拘泥于“拐杖,手杖”,应是“随身的木棍或竹竿”。整句翻译:“用棍子扑打荒草灌木(开路),随地游玩,随时休憩。”[11]综上所述,若“扶老”为拐杖,对正值壮年且刚刚脱离“尘网”的内心愉悦的陶渊明来说,似乎不相符合。若“扶老”是随身的木棍或竹竿,更能正面诗人已经走出庭院,走进了广阔的自然。
因此,诗人走出庭院便有了依据,虽然庭院内榆柳、桃李、松菊一用俱全,景色繁盛,柴门紧扣,诗人常在庭院中流连,但仰观之远景,白云悠然、归家的鸟儿、孤松的轮廓、徘徊的光影,勾人心魄。诗人拿着棍子扑打荒草灌木,不时抬头看看,加快了步伐。
三、 缘情据理,合理考究
(一)抚孤松而盘桓的是遐观之“景”
诗人在小序中叙述自己辞官的原因:“质性,……得”“违己”“深愧……之志”。总结原因即本性坦率自然,无法造作勉强自己。文中“世与我……,……焉求”则表现出世俗的背离让诗人放弃了做官的念想,回归田园。由此,我们推断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回归自我的表现。尽管文中有些句子不乏痛苦矛盾,如“引壶觞……酌”流露出与世隔绝的孤独;“哀吾……休”感叹生命的短暂;“聊……尽”传达出不能主宰命运的无奈,但无碍文章的愉悦乐观的情感基调。
首段“舟遥遥”四句,将作者摆脱官场桎梏、复返自然的畅快和归心似箭含蓄的表达出来。在写归家后的生活情趣时,诗人创设了一个自由自在、闲适安乐的意境。回归田园,与亲戚交往、弹琴诵书、车舟出游、躬耕农亩、赋诗放歌,其基调仍是乐观旷达的。末段开头以三个感叹句和末尾的“乐夫……疑”强烈地表达出诗人的处事态度和人生哲理。诗歌的每个部分传达出情感基本一致:乐。由此,若诗人在第二段末尾远观“摇摇欲坠”的日光,“抚……桓”,“孤”“盘桓”二词便为第二段末尾蒙上了一层触景自伤、寂寞迷茫的暗纱,与上下文营造的愉悦乐观基调不符,所以笔者赞同王启钢(2010)的看法,是诗人遐观的日光在抚孤松徘徊并非诗人。
因此,无论诗人是在庭院内还是庭院外,抚孤松而盘桓的都是日光,笔者“遐观“景”,诗人于庭院中手抚孤松盘桓”这一假设不成立。
(二)诗人走出庭院,见日光徘徊在松间
人教版语文必修5《教师教学用书》中称作者从写居室转到了写庭园,甚至到高处、远处等目光所及之处,并选取了‘园……涉’‘策杖流憩’‘抚孤松’‘出岫之云’‘知还之鸟’等几个画面,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写庭院的是“园日涉”,所见之景为“出岫之云”“知还之鸟”。同样我们可以推测吴战垒所述的第二段中由居室写到庭院也止于“园日涉”这一句,流连忘返的景色也许就在庭园之外。据人教版必修5教材、《教师教学用书》《国语词典》对于“游憩”一词的释义,“周游”“到处游息”的解释更适合广阔的场景。据我们对于陶渊明诗歌中对田园居的描述,对于“扶老”的解读,庭院外的自然风光似乎更能满足诗人四处赏玩的目的。同时,诗人在庭院外游玩,也与下文走到外出耕种、游赏有语意的衔接,过渡得更加自然。从庭院内走向庭院外更广阔的自然,使文章在结构铺排上更加精巧绵密。
当诗人走出庭院,便无法手抚庭院内的松,而所仰观之山上的青松又非近在咫尺,而在远山之上,抚孤松而盘桓的便不能是诗人自己,只能是将要落下的不忍离去的日光,所以笔者的第二种假设成立。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诗人归家后的游踪应是归家——居室内——庭院外。《归去来兮辞》中,归家后的诗人从庭院的“日涉”踱步走出庭院外 “流憩”,矫首遐观,望见无意从山头升腾的云气,因疲倦而飞回的鸟儿,在孤松徘徊的暗淡日光。
作者:王蕾
- 上一篇:《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形象新解
- 下一篇:群贤论文登金榜 教坛名师竞风流